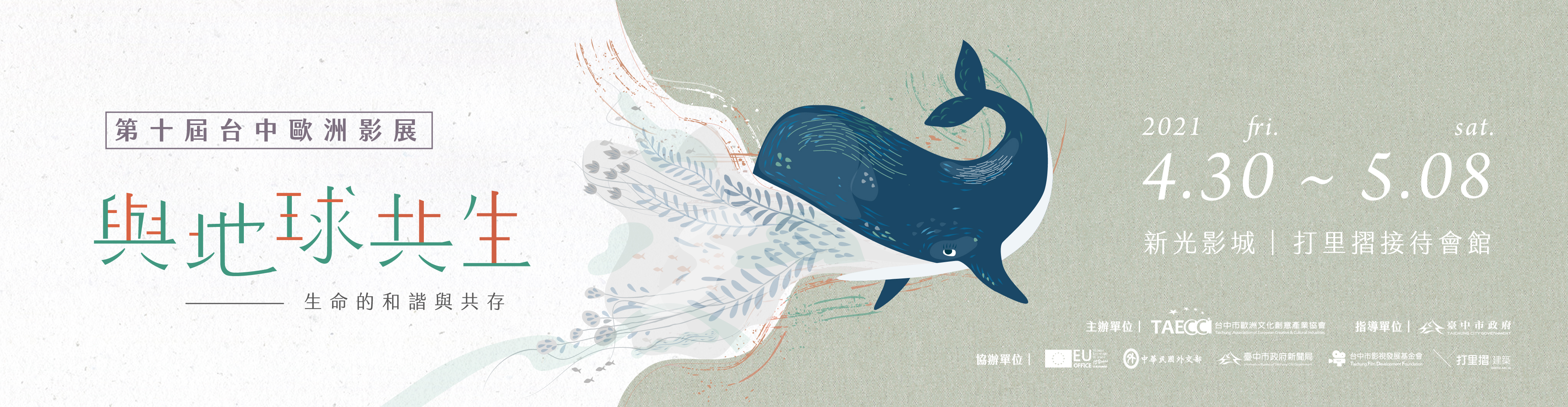貝多芬在「命運來敲門」的第五號交響曲後,創作了如詩歌般甜美的《田園交響曲》,透露著作曲家對於生命與大自然的沈思。我也有自己的田園交響曲,那是一段關於林中冒險的小小故事。
1998年大學音樂系剛畢業,我初到木橋國中擔任老師的第一天,班上連一個人都沒有。
我跑到操場要去找他們,他們肯定還在貪玩,不肯回來。心中才這樣尋思,教務主任就氣喘吁吁跑來跟我說:「不好了,昨夜山中大雨。連結部落和學校的唯一橋樑崩了。孩子過不來了。」
真是意外的打擊。我還沒跟這群小孩照過面呢。
「沒有辦法過去看他們的狀況嗎?」,我問。
「車子是過不去了。但有條森林小路慢慢走,從現在出發,大概傍晚前可以到。」
也不知那裡來的勇氣,我堅持要到橋的彼岸看他們。
「路是不難走。但山裡的狀況不明,常常一下子就變天。你剛來我們學校報到沒多久,還是不要冒著這個險比較好。」主任的語氣顯得擔憂。
我堅持要跋涉去看他們。天底下沒有任何導師,在開學第一天,連孩子的眼睛都還沒看到。
主任說,往下游走,順著河,我的學生都在那裡。
我把孩子的名冊帶上,還有一把吉它。萬一我迷路了。飄逸悠揚的吉它聲,可以在山裡傳得又深又遠。
「山裡的孩子都喜歡音樂吧」,我想。第一次見面,不要用生冷教材開始。用溫暖,用一點點好聽的聲音。我想我可以在音樂中告訴他們一些什麼。
順著河,主任說,感受山林之彼端,你的孩子在翹首盼望著你的到來。但要一直趕路,天若黑了,就很難自己走出來。森林有它自己的祕密和絕域。切莫亂闖。
路果然不難走。沒有太多曲折的狹彎。昨夜漲到滿位的河,如今平息而安穩地流動著,就好像什麼也沒發生過。
輕風徐來,林中有鳥獸鳴叫,我想像王維的詩篇,或是莫內的印象畫,是那樣的自在舒心,那樣地引人入勝。
我想像這些孩子們多麼幸福。在山林間奔跑和嬉戲的樣子。那是他們的腳步。他們的日常。他們是天地養育出來的一齣盛大歌劇,而每一個都是生命中的主角。
我來這裡,帶著一本名冊,想要在相逢的時刻,以老師的祝福,在雨夜過後,當天地間的橋斷了,輕聲如魔法般地,召喚出他們的名字。
塔雅斯.努曼
本多.藍波安
提香.阿斯馬庫
每個發亮的名字。 每顆期待相認的心。
未曾蒙面,孩子們模糊的臉,在我腦海裡有最鮮明的輪廓。
那可能是在秋收的某個晚上,他們牽著手,圍著柴火燒得光亮的夜空裡,聽見祖靈在歌唱。
又或者像這樣前一個大雨滂沱的微光時刻裡,橋不見了。孩子們顫抖卻又無比溫柔地依偎在一起。他們或許窮得只剩下彼此和夢,但夢是最珍貴的東西。
樹林裡每隻蟲叫都傳達了想念。每片落葉被輕輕踩碎的聲音,都包含著亙古以來小小生滅的微觀宇宙。
我來這裡,滿心期待要以大學四年書上所習得的學問,用音樂感動他們。卻沒想到,是途經小花小草的盛開,那些山林裡無語的音樂,讓我先被生命感動了。
我突然想起「焦尾琴」的故事。
相傳古代有製琴師為求一良木製琴而不可得,有日上山,竟聽得木頭在燃燒的聲音,低鳴而悲切地哀嚎著,像是懇求著被什麼人聽見。
他聽見了,那個懷有雅願造琴的男人。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相逢時,卻充滿了傷痕。
1998年大學音樂系剛畢業,我初到木橋國中擔任老師的第一天,班上連一個人都沒有。
我跑到操場要去找他們,他們肯定還在貪玩,不肯回來。心中才這樣尋思,教務主任就氣喘吁吁跑來跟我說:「不好了,昨夜山中大雨。連結部落和學校的唯一橋樑崩了。孩子過不來了。」
真是意外的打擊。我還沒跟這群小孩照過面呢。
「沒有辦法過去看他們的狀況嗎?」,我問。
「車子是過不去了。但有條森林小路慢慢走,從現在出發,大概傍晚前可以到。」
也不知那裡來的勇氣,我堅持要到橋的彼岸看他們。
「路是不難走。但山裡的狀況不明,常常一下子就變天。你剛來我們學校報到沒多久,還是不要冒著這個險比較好。」主任的語氣顯得擔憂。
我堅持要跋涉去看他們。天底下沒有任何導師,在開學第一天,連孩子的眼睛都還沒看到。
主任說,往下游走,順著河,我的學生都在那裡。
我把孩子的名冊帶上,還有一把吉它。萬一我迷路了。飄逸悠揚的吉它聲,可以在山裡傳得又深又遠。
「山裡的孩子都喜歡音樂吧」,我想。第一次見面,不要用生冷教材開始。用溫暖,用一點點好聽的聲音。我想我可以在音樂中告訴他們一些什麼。
順著河,主任說,感受山林之彼端,你的孩子在翹首盼望著你的到來。但要一直趕路,天若黑了,就很難自己走出來。森林有它自己的祕密和絕域。切莫亂闖。
路果然不難走。沒有太多曲折的狹彎。昨夜漲到滿位的河,如今平息而安穩地流動著,就好像什麼也沒發生過。
輕風徐來,林中有鳥獸鳴叫,我想像王維的詩篇,或是莫內的印象畫,是那樣的自在舒心,那樣地引人入勝。
我想像這些孩子們多麼幸福。在山林間奔跑和嬉戲的樣子。那是他們的腳步。他們的日常。他們是天地養育出來的一齣盛大歌劇,而每一個都是生命中的主角。
我來這裡,帶著一本名冊,想要在相逢的時刻,以老師的祝福,在雨夜過後,當天地間的橋斷了,輕聲如魔法般地,召喚出他們的名字。
塔雅斯.努曼
本多.藍波安
提香.阿斯馬庫
每個發亮的名字。 每顆期待相認的心。
未曾蒙面,孩子們模糊的臉,在我腦海裡有最鮮明的輪廓。
那可能是在秋收的某個晚上,他們牽著手,圍著柴火燒得光亮的夜空裡,聽見祖靈在歌唱。
又或者像這樣前一個大雨滂沱的微光時刻裡,橋不見了。孩子們顫抖卻又無比溫柔地依偎在一起。他們或許窮得只剩下彼此和夢,但夢是最珍貴的東西。
樹林裡每隻蟲叫都傳達了想念。每片落葉被輕輕踩碎的聲音,都包含著亙古以來小小生滅的微觀宇宙。
我來這裡,滿心期待要以大學四年書上所習得的學問,用音樂感動他們。卻沒想到,是途經小花小草的盛開,那些山林裡無語的音樂,讓我先被生命感動了。
我突然想起「焦尾琴」的故事。
相傳古代有製琴師為求一良木製琴而不可得,有日上山,竟聽得木頭在燃燒的聲音,低鳴而悲切地哀嚎著,像是懇求著被什麼人聽見。
他聽見了,那個懷有雅願造琴的男人。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相逢時,卻充滿了傷痕。
繼續閱讀文章
他奮不顧身,躍入火堆裡,要把這塊素玉之木,從荒涼裡搶救了出來。回家後焚膏繼晷地傾注生命所有的力量,終而製得這把舉世無雙的焦尾琴。曾經被以為是「腐木而不可雕也」的生命故事,竟然挺著揚拔的意志,活了下來。那尾部被燒灼的痕跡,在每個夜裡發出了撫動心絃的色彩,聞者無不潸然落淚。
是這樣子的嗎?
到木橋國中報到前,他們告訴我,這是一群被放棄的孩子。只要讓他們好好長大,不犯法惹事,就是你來這裡的唯一目的。
其實他們也早早就把我放棄了。
一個音樂老師?妄想在窮鄉僻壤中種下什麼嗎?讓主修音樂的傢伙擔任導師不正說明了一切?這裡太缺人了,沒有正科生會來,缺到只好讓最邊緣的人來這裏一展長才。而他們看我的眼神,早就宣判了我肯定「沒有演奏才華」才會淪落到這裡:成為一個老師。
想到這裡,突然也就領悟了今天早上,內心為什麼有那樣的聲音,告訴我一定要踏上這個孤獨內省的林中之路。
因為我想找到他們。
一群不被怎麼期待的孩子,在橋塌了的這一天,期待上學,期待被找到,希索一點點人們的溫柔和慎重。正如同我自己也想被什麼人找到一樣。
天不知怎麼突然暗了。我想起魔神仔的傳說。我還沒走出這裡,但我並不害怕。
據說魔神仔抓走的都是絕望的人,那些在人世間找不到愛的被棄者。他們不斷想向什麼人訴說夢想,得到的卻只有自己的回音,因為從來沒有人認真在聽。寂寞填滿了內心被蟲攀爬的廢墟,此處正是外魔得以入侵的所在。
但我還沒有絕望,縱使他們看我的眼神是那樣。我還有愛,也還有一點點愛人的能力。
這片山林正在回應我的思考,以無比寬慰的擁抱和看似寂靜裡的細微跫音。
在河的不遠處,那橋塌了的彼岸,肯定還有什麼人在等我。
我已經聽見泥土的渴望。
而種子正在歡呼著園丁的到來。
這群山林的孩子在城鄉差異巨大化的台灣,原本是「不被祝福的一群」。但那又怎樣呢?導演Danny Boyle的《貧民百萬富翁》說,你可以窮,你可以是他們眼中的underdog,但永遠不要忘了,“the future is to be written”。 換句話說,未來還沒寫下,此刻仍是你的,你還有讓自己的音樂被聽見的可能。
是誰先聽見了這群孩子內心的聲音,遠在這個世界聽見那樣的純然與真摯呢?他們的老師陳珮文和王子建先生。只是因為孩子的一句「老師,這是甚麼? 我想學這個,可以教我嗎?」開始義無反顧地投入這群孩子的人生。
她和她丈夫王子建兩人自掏腰包,籌措經費讓原鄉孩子們學提琴、上音樂班、參賽、成立親愛愛樂、成立基金會、成立學校,甚至照顧了幼稚班、國小、國中高中畢業後音樂班孩子的生活起居。
這是何等的奉獻和溫柔?明知「音樂無盡,話語有時而窮」,再多的墨水也未能傳達內心全部的感動,也要振筆為文,為這群可愛的孩子和他們可敬的老師,寫下一點放歌生命的《田園交響曲》吧。而如果這首曲子有副標,我想,那肯定是愛。
是這樣子的嗎?
到木橋國中報到前,他們告訴我,這是一群被放棄的孩子。只要讓他們好好長大,不犯法惹事,就是你來這裡的唯一目的。
其實他們也早早就把我放棄了。
一個音樂老師?妄想在窮鄉僻壤中種下什麼嗎?讓主修音樂的傢伙擔任導師不正說明了一切?這裡太缺人了,沒有正科生會來,缺到只好讓最邊緣的人來這裏一展長才。而他們看我的眼神,早就宣判了我肯定「沒有演奏才華」才會淪落到這裡:成為一個老師。
想到這裡,突然也就領悟了今天早上,內心為什麼有那樣的聲音,告訴我一定要踏上這個孤獨內省的林中之路。
因為我想找到他們。
一群不被怎麼期待的孩子,在橋塌了的這一天,期待上學,期待被找到,希索一點點人們的溫柔和慎重。正如同我自己也想被什麼人找到一樣。
天不知怎麼突然暗了。我想起魔神仔的傳說。我還沒走出這裡,但我並不害怕。
據說魔神仔抓走的都是絕望的人,那些在人世間找不到愛的被棄者。他們不斷想向什麼人訴說夢想,得到的卻只有自己的回音,因為從來沒有人認真在聽。寂寞填滿了內心被蟲攀爬的廢墟,此處正是外魔得以入侵的所在。
但我還沒有絕望,縱使他們看我的眼神是那樣。我還有愛,也還有一點點愛人的能力。
這片山林正在回應我的思考,以無比寬慰的擁抱和看似寂靜裡的細微跫音。
在河的不遠處,那橋塌了的彼岸,肯定還有什麼人在等我。
我已經聽見泥土的渴望。
而種子正在歡呼著園丁的到來。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
2019年衛武營剛落成不久,我有幸在號稱全亞洲最美的葡萄園式音樂廳感受來自台灣土地最真摯的呼喚。那是由「親愛愛樂」演出的《14堂山上的音樂課》。我非常感動,訝異於這群孩子的作曲和演奏能力。但技巧之外,我聽到的是遠比音符自身更多的東西。那是來自故鄉山林的感召,才可能滋生發養的音樂直覺。沒錯,這些孩子不是在表演音樂,遠不只perform而已,他們在試著和這個世界connect,要用每把最深情的提琴,告訴你他們的生命故事。這群山林的孩子在城鄉差異巨大化的台灣,原本是「不被祝福的一群」。但那又怎樣呢?導演Danny Boyle的《貧民百萬富翁》說,你可以窮,你可以是他們眼中的underdog,但永遠不要忘了,“the future is to be written”。 換句話說,未來還沒寫下,此刻仍是你的,你還有讓自己的音樂被聽見的可能。
是誰先聽見了這群孩子內心的聲音,遠在這個世界聽見那樣的純然與真摯呢?他們的老師陳珮文和王子建先生。只是因為孩子的一句「老師,這是甚麼? 我想學這個,可以教我嗎?」開始義無反顧地投入這群孩子的人生。
她和她丈夫王子建兩人自掏腰包,籌措經費讓原鄉孩子們學提琴、上音樂班、參賽、成立親愛愛樂、成立基金會、成立學校,甚至照顧了幼稚班、國小、國中高中畢業後音樂班孩子的生活起居。
這是何等的奉獻和溫柔?明知「音樂無盡,話語有時而窮」,再多的墨水也未能傳達內心全部的感動,也要振筆為文,為這群可愛的孩子和他們可敬的老師,寫下一點放歌生命的《田園交響曲》吧。而如果這首曲子有副標,我想,那肯定是愛。
延伸聆聽